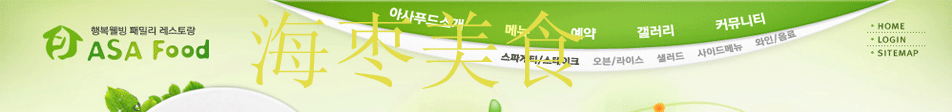|
点击
年3月20日,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纪念日。天翻地覆的西藏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古老土地,从此翻开历史全新的一页。短短六十载,跨越上千年。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当家做了主人,开启了西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光辉历程。走进今天的新西藏,雪山依旧,却换了人间。 年7月9日,是我们大学毕业离开母校哈尔滨师范大学40周年纪念日。 40年前,我们34位同学完成学业,打起背包,肩负使命,告别母校,吻别故土,走向西藏,投身于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和发展事业。 40年后的今天,我们把青春留在了西藏,我们的灵魂也留在了西藏。西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友谊,我们的故事,都充满着浓浓的西藏情结,炫染着格桑花的色彩。 如今,我们已年过花甲,但是西藏岁月的记忆,却从来未曾模糊。 有一首歌曲《老西藏》这样唱道: “轻轻的叫您一声老西藏 您来了 就把根留在了西藏 献了青春献子孙 轻轻的叫您一声老西藏 您来了 就把心留在了西藏 献出忠诚献生命 多少年的风霜 露出了脸上的高原红 多少人的青春 就是酥油茶的味道 多少人的朋友 就是太阳下的兄弟 无论在与不在 无论走与不走 您们把生命种在这里 花开的时候 轻轻的叫您一声老西藏 老西藏!” 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热泪盈眶,勾起难忘的回忆。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西藏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从全国各地一些重点大学,包括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陆续选派一些优秀毕业生,进藏支援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但是数量不多。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教育部委托内地10个省市,包括两山(山东、山西)、两河(河南、河北)、上海、江苏、湖北、黑龙江、陕西、四川的10所高等院校分别为西藏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派遣不同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支援西藏。 年9月,黑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通过层层推荐,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农村选拔了70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进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数学系,为西藏培养师资。我们有幸被推荐选拔,成为中文系西藏班学生。 年7月初,我们顺利完成学业。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西藏班的34名毕业生和数学系西藏班同学一起,由学校副校长贾仰周、中文系党总支书记顾家骥、辅导员曹祖亢、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柴树朋等同志带队,随行一名校医,从东北哈尔滨向祖国的西南边疆---西藏出发。 学友袁晶明大姐含泪久久地拥抱着我深情地说:“好妹妹,我们真的就要分别远在天边了,我会惦念你的!思念,只能梦中相见。真盼啊,盼望妹妹快回来,盼望我们再相见!” 学友一兵在送给我的笔记本上写道: “愿你做—— 凌冰怒放的雪莲, 击天翱翔的雄鹰!” 记得从哈尔滨出发的那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学校的许多老师、同学、校友都自发地冒雨前往火车站为我们西藏班送行。站台上,雷声、雨声、广播声、告别声混杂在一起震耳欲聋,雨水、泪水洗刷着一张张送别的脸庞。 由于当时信息渠道的局限性,人们对西藏情况了解甚少。记得曾经看过电影《农奴》,是一部反映西藏农奴制度的故事片。影片描写了在旧西藏野蛮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小奴隶强巴过着非人的生活,装成哑巴,他用无声来表示反抗。解放军进藏后,治好了强巴的病,他揭露了奴隶主阻挠西藏解放的罪行,并多次在危急中被解放军所救。农奴获得彻底解放,强巴终于开口说话。从电影中看到了西藏实景的雪山,知道了旧西藏的残酷与黑暗。但是现在的新西藏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都不知道,这次出发,前方路途有多远?这次告别,何时才能再回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送别场面,不仅热烈,还颇有一点儿悲壮感。 随着车轮缓缓启动,我们开始了奔赴西藏的漫长旅程。
我们进藏的旅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离开家乡到北京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我和绝大多数同学坐的是硬座,只有几个身体比较弱的女同学被照顾睡的卧铺。远行之始,大家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家乡故土,在兴奋与留恋中,时间过得很快,似乎并没有感觉到累,第二天就到了首都北京。 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教育部领导向我们介绍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党和国家对西藏建设发展的英明决策以及青年大学生支援西藏的光荣使命和重要意义,勉励我们克服困难,在雪域高原为建设西藏做出贡献。我被指定作为学生代表在座谈会上表态发言:决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希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青春年华。 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崇文饭店。先后组织我们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参观游览了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颐和园、长城等名胜古迹、著名景点,还观看了一场精彩的国家级水平篮球赛。 二从北京到柳园一周以后,我们从北京坐上火车,继续往西藏方向进发,驶向第二个目的地——远在甘肃西部的柳园车站。由于路途遥远,全体同学都是卧铺。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高铁,老式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速度很慢,大站小站都要停。经过三天两夜的行驶,穿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我们到达了柳园。 柳园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东迎嘉峪关,西通新疆哈密,南与敦煌相接,北与肃北马鬃山相连,是连接甘、青、新、藏四省区的陆路交通枢纽,素有“旱码头”之称。 茫茫戈壁滩上的柳园,吃水难、用水难程度超乎想象,完全依靠火车从外地把水运到柳园火车站,储备起来,人们吃水用水都要到火车站去拉水,所以在那里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滴水贵如油”。 我们住在西藏交通厅驻柳园转运站。刚到的时候,由于我们不知道缺水,青年学生爱干净,洗手洗脸洗衣服一如在家那样哗哗地用水,被转运站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惜在心上,急忙跑过来告诉我们水的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节省用水。后来我们用水就很仔细了,用脸盆端一点水,先洗脸,然后不马上倒掉,继续留着洗手洗衣服或者洗脚用。 柳园属于干旱地区,当地种植不了青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很少吃到青菜,多是食用干菜和罐头、腊肉等。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腊肉炒腐竹,不好吃。还有一个菜名叫“蚂蚁上树”,其实就是粉条炒腊肉丁,只觉得腊肉的味道怪怪的,真难吃啊! 西藏派来接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到达,我们只好一边等待,一边休息。同学们还是有吃苦准备的,并且一直在积极想办法。 有些同学听说西藏没有菜吃,就在柳园买了不少咸榨菜疙瘩,在房前空地上铺起旧报纸,把榨菜疙瘩晒干,准备带到西藏当菜吃。几天后,榨菜疙瘩表面出现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并慢慢生出一层绿毛,开始腐烂变质,难闻的异味招来苍蝇嗡嗡乱飞。买咸榨菜的做法宣告失败。 又听说西藏物资匮乏,有些东西买不到,许多同学赶紧跑到柳园当地那个不大的商店去买了很多生活必需品。我买了十几包卫生纸,十几块肥皂,两瓶雪花膏,装了满满一个手提包。心里核计着,到了西藏省着点用,应该能够两年用的了。 后来我们到了西藏才知道,西藏其实是有商店的,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因为当时我们对西藏的了解太少,才闹出许多类似的笑话来。 一周以后,接我们的汽车到了。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政治部副主任李发祥同志和拉萨市文教局的杜科长来接我们。李主任首先宣布了第一批分配名单,其余同学到达拉萨以后再宣布。第一批分配名单中,我们班有5人分配到格尔木西藏办事处,4人分配到那曲地区,2人分配到西藏民族学院。 三穿越青藏线去西藏,再往前已经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青藏公路蜿蜒伸向遥远的天边。当时的青藏公路担负着百分之八十的进藏物资运输,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 我们转乘汽车,朝着目的地——西藏拉萨方向,艰难地行进着。那时候的青藏公路是沙土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行驶的汽车上下颠簸,我们的身体随着汽车大起大落,忽而脑袋撞到车顶上,忽而又重重地跌落下来。前边不知道是谁的头被撞疼了,“啊”地叫一声;后边又不知道是谁的屁股被摔得太疼,忍不住咧嘴深沉地“哼”一声! 汽车行驶一整天,夜幕中到达了历史文化名城——敦煌。提起敦煌,很多人脑海中自然就会浮现出漫天的黄沙、莫高窟里边的“飞天”与古佛、浓浓的西域风情。敦煌古城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也是进入新疆、西藏的门户,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 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李主任组织同学们集体参观了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往曾经在书中看过,这次如能亲临近前欣赏,那将是何等不同寻常的感受啊! 可是,因为赵洪平、柳春燕二位同学原计划将要在敦煌举行婚礼,为了筹备他们第二天的婚礼,我没有去参观莫高窟。结果赵洪平、柳春燕却又由于异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证明不全的原因,在敦煌没能顺利登记,故推迟了敦煌婚礼。 我们告别送行的学校领导和分配到西藏民族学院的同学,汽车继续前行。 窗外是湛蓝的天空,美丽的流云。我们新奇地看着远方群山连绵,观赏各色云彩变幻。汽车一路爬坡,前方已经远远看见当金山。当金山西接阿尔金山,北接祁连山,面对昆仑山,山势巍峨雄伟。在驼铃声声的古代,当金山曾是丝绸之路必经的重要山口。越过海拔多米的当金山口,就要进入青藏高原了。 这时候,突然迎面开过来几辆汽车,一边鸣笛一边大声呼喊着示意我们停车。原来,前方发生了险情,祁连山突发特大洪水,路桥已被冲毁不能再往前走,让我们赶紧往回撤。我们的汽车立刻掉头往回开,就这样一场大水把我们再一次赶回了柳园。 在柳园又等待了一周时间,直到洪水退去,道路修通,我们的汽车才再次出发。沿途经过敦煌、当金山、鱼卡、大柴旦、德令哈,8月4日到达格尔木。“格尔木”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格尔木地处青海省西部、青藏高原腹地、欧亚大陆中部,昆仑山、唐古拉山横贯全境,山势高峻,气势磅礴,雪峰连绵,冰川广布,冰塔林立,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是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盐湖碱滩沼泽众多,察尔汗盐湖是世界最大的盐湖,号称“盐湖之王”。格尔木是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中转站。 分配到格尔木的赵洪平、柳春燕、刘忠伟、关德范、穆艳芬等五位同学就在这里报到了,格尔木中学校长彭隆全同志率领学校全体干部教师热情欢迎这些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们。 第二天,在格尔木办事处中学礼堂,我们全班同学和格办中学的老师们一起为同窗情侣柳春燕、赵洪平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虽然没有披上婚纱、也没有拍下照片,但是,圣洁的雪山和蓝天白云见证了他(她)们牵手一生的婚礼!学校为他们准备了新房、新被子、新床单、新枕巾,同学们还凑钱买了生活用品送给新郎新娘,祝福他(她)们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生活幸福! 8月6日,我们告别了留在格尔木的同学继续向前进。过了格尔木,汽车在海拔越来越高的青藏公路上奔驰。沿途经过了西大滩、沱沱河、雁石坪、五道梁、唐古拉山,爬上海拔米的唐古拉山口(唐古拉山顶最高处海拔多米)。“唐古拉”,藏语是“高原上的山”,蒙语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山上终年白雪皑皑,风雪交加,号称“风雪仓库”。唐古拉是青海和西藏的分界线,山口处建有纪念碑和标志碑,是沿青藏公路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也是长江的发源地。我们行进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上。抬眼望去,虽然时值盛夏,可是这里的江河凝聚为晶莹的冰川,浪花沉默成无言的冰雕,静静地安眠着。山口气候极不稳定,即使夏天,公路也经常被大雪封锁,冰雹霜雪更是常见现象,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六成。 气候越来越恶劣。由于连日长途坐车的疲惫,同学们渐渐感到缺氧严重,陆续出现恶心、呕吐现象,有人开始吸上了氧气。我的体质算是好的,在五道梁兵站的时候有点反应,但是也不像别人那样反应强烈,只是有些头晕和恶心。 李主任和杜科长细心地照顾我们,为了能让同学们喝上开水,他们趁着汽车停下休息一会儿的空隙时间,跑到河边去刨冰铲雪,用汽车上的汽油喷枪,烧开水给大家喝,温一桶热水供同学们洗手洗脸用,让同学们感到很温暖。 我和穆常丽的座位挨在一起,我们俩互相作伴,互相照顾着。寂寞的时候,我们俩就轻轻地哼支歌曲,既减轻孤寂,又不打扰其他同学。王照全坐在我们的后排,看到我的头发上有很多尘土,主动摘下自己头上的军帽,让我戴上。他还把自己的手电筒让给我们女生用,方便我们在夜宿兵站时上厕所照路用。 风尘仆仆行驶一天,到了晚上下车时,同学们头上脸上全身都是灰土,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 我们就这样在青藏公路上日行夜宿,早晨天不亮从兵站出发,黑天以后赶到下一个兵站食宿。全程翻越了四座大山——昆仑山(米)、风火山(米)、唐古拉山(山口海拔米)、念青唐古拉山(米);跨过了三条大河——通天河、沱沱河、楚玛尔河,平均海拔米。穿过了藏北羌塘草原。 我们行进在青藏公路上,虽然有恶劣气候的考验,有严重缺氧的不适,有数日乘车的疲惫,有刺骨的风雪交加,也有汽车抛锚带来的恐慌……,但是那苍莽逶迤的昆仑,浩瀚无边的无人区,一望无际的盐湖,高原圣湖纳木错,那曲当雄大草原,随处可见的牦牛羊群,还有那散落在草原上的帐篷、经幡,玛尼堆,令人訇然震撼,心旌摇荡,一种自然升腾而又超越自我的感受,坚定着我们这支顽强的进藏队伍。 翻过唐古拉山,进入西藏,过了安多,到达那曲。我们班的叶小元、蔡丽华、蔡觉权、张学东四位同学留下报到。 那曲地区地处西藏自治区北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藏北”。西靠阿里,东临昌都,北接新疆和青海,整个地区位于可可西里、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平均海拔米以上。叶小元、蔡丽华、蔡觉权、张学东四位同学留在了艰苦的那曲地区工作,他们无怨无悔,一到那曲,就毅然报到了。 余下的其他同学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坐上汽车继续前进,当天夜里终于抵达目的地——拉萨。那是年8月9日。
拉萨,我们终于到达西藏拉萨了!
到达拉萨的当天晚上,我们被安排住在自治区工业厅招待所。招待所的院子里开满了鲜艳的花,有黄色的、粉红色的、青绿色的。花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的像蝴蝶,有的像小葵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啊?想不到拉萨还有这么美的花呀!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打听这是什么花儿?接待我们的丹增朗杰同志告诉我们说,这叫格桑花。哦!原来这就是格桑花,传说中的格桑花! 七月的拉萨,正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丹增朗杰告诉我们,在藏语中,“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以来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格桑花也是高原上生命力最顽强的野花的代名词。 很多拉萨人把格桑花又称为“张大人”花,据说,此花是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带到拉萨的。年,张荫棠进入西藏时曾带入各种花籽,试种后,其他花籽无法生长,唯有一种花籽长出来呈“八瓣形”,且耐寒,花瓣美丽,颜色各异。一时间,拉萨家家户户都争相播种。这种花生命力极强,自踏上这片高天阔土,就迅速传遍西藏各地。可是谁都不晓得此花何名,只知道是驻藏大臣张荫棠大人带入西藏,因此起名“张大人”。时至今日,每家门前只要有点空地,都喜欢种一片格桑花,鲜艳美丽,寄托着向往幸福的愿望。藏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管是谁,只要找到了八瓣格桑花,就找到了幸福。 同学们经历了长途颠簸劳顿的历练和数日高原缺氧的考验,到达拉萨后经过短暂休息,很快就适应了气候。我们百听不厌的一首藏族歌曲是张振富、耿莲凤演唱的《逛新城》,一到拉萨,大家就急不可耐地也想逛逛新城。教育厅政治部负责接待我们的丹增朗杰、吕学国等同志带领大家参观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逛了八廓街。 初到拉萨,映入眼帘最高大、最雄伟的建筑当属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坐落于红山之顶,依据山势蜿蜒垒砌到山顶,群楼重叠,殿宇嵯峨,气势雄伟。布达拉宫是吐蕃第33任赞普松赞干布迁都拉萨时所建相传也是藏王松赞干布为迎娶远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建筑,是西藏最庞大、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也是第五套人民币50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在蓝天雪山的陪衬下,布达拉宫格外壮丽,仿佛是圣洁和庄严的化身。 布达拉宫脚下的拉萨市区,面积不大。位于拉萨老城区中心的大昭寺,据称是藏王松赞干布时期由尼泊尔公主提议,文成公主占卦定点修建的一座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已有多年的历史。由于后期一直主供文成公主带进西藏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金象,故称“拉萨佛殿”,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以大昭寺为中心辐射出的外围街道叫八廓街。大昭寺广场转经朝拜的人流潺动,飘袅的桑烟,沁心的藏香,醉人的酥油茶香,充满浓郁的藏族生活气息,呈现着一派向善、平静、吉祥、和谐的景象。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拉萨的主要街道是水泥路面,城关小巷多为沙石路。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百货公司、民居等建筑大多是平房。靠近八廓街的地方,多是藏式土木房屋。稍远些新建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多是铁皮屋顶,远远看去,闪闪发光,在蓝天白云雪山的辉映下,构成一幅特色鲜明的雪域风景画。 分配方案宣布了。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各地市和自治区有关厅局所属中学。王惠生分配到拉萨市文教局,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教育厅。很快,同学们陆续被各地市、厅局单位派车接走了。同学们就像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撒向西藏各地。 这一别,有不少同学就再未见过面,直至年8月16日中文系西藏班同学毕业四十年回到母校相聚谢师恩。40年间,虽然距离遥远,但我们始终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后来不论是坚守高原成为“老西藏”的,还是因为个人身体或家庭困难陆续调回内地的,我们班同学的心始终被浓浓的西藏班情结凝聚在一起,不管谁走到哪里,只要有老同学,就有我们的“家”。 年7月8日,我在《献给76级中文系“校友录”》中写道: 在年的秋季, 我们于哈师大中文系西藏班相聚。 虽然彼此都很陌生, 但又似乎那样熟悉。 来自不同地方, 各自不同经历,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志愿为建设新西藏尽力。 从此, 你认识了我, 我熟悉了你, 一个崭新的环境, 我们组成了新的集体。 在这里, 我们不但有了班主任、辅导员, 而且有了班长和书记。 四个小组, 宛若四个方队, 每位同学都尽情挥洒青春与活力。 我们笑过、哭过、吵过、闹过, 甚至谁和谁还打过…… 一切的一切, 如今都是美好的回忆; 所有的所有, 都将永久存储在我们的脑海里。 年轻的故事真好,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显珍贵。 转眼几十载过去, 当年的青丝已成两鬓华发, 天各一方的我们, 生出越来越深的牵挂! 期待着雪域高原再相聚, 西藏班的历史档案中, 将记下重重的一笔。 让我们互相祝福, 好人一生平安! 让我们共同祈愿: 西藏的明天更美! 永不停息的雅鲁藏布江水,波涛滚滚,一直向前,向前……。 40个年头,仿佛眨眼的瞬间。经历过岁月的洗涤,渴望心静如水的感觉。然而,打开尘封的记忆,那些似乎已被遗忘的往事,竟然还是历历在目—— 回首40年,哦——西藏,我们一直在与你同行! 曾记得,公元年,大学毕业之初,怀着北方姑娘特有的泼辣和好奇,简装西行; 曾记得,翻越唐古拉穿越青藏线时,八天八夜的汽车颠簸、高原反应、脑袋的胀痛和满身的尘土; 曾记得,第一次圆满完成任务时的兴奋和自信; 曾记得,第一次下乡被烈马甩下的尴尬和疼痛; 曾记得,第一次品尝酥油茶、喝青稞酒、吃生牛肉时的感觉; 还有多少曾记得,还有多少的忘却,让我们慢慢想起…… 40年,我们经历了什么? 是从铁皮平房到高楼大厦,还是从泥巴路到柏油路的变化? 是从青藏公路到铁龙天路的延伸,还是从有线电话到程控光纤宽带互联网的面对面? 是从罐头、蛋粉、腊肉到一片片绿色大棚里的新鲜蔬菜,还是从衣服单调的青灰蓝到赤橙黄绿的多姿多彩? 比比皆是的巨大变化,让古老的青藏高原焕发出与祖国同步的盎然生机! 40年,我们庆幸自己能够与祖国西藏共同进步; 40年,亲眼见证了西藏改革开放的一幕幕壮阔波澜; 40年,亲身经历了改变西藏人民生活的一个个大事件; 40年,西藏的发展变化,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一个真理:国家兴则民族兴,民族团结则国富民安! 40年,许许多多“老西藏”,还有我们的各族同事、朋友们,和百万西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地牺牲着健康、爱情、亲情,在雪域高原谱写着青春的赞歌,铸就着人生的辉煌,奉献出血汗甚至生命。他们都是顽强而又美丽的格桑花! 40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暮年的我们乌丝生华发,但是仍然初心不改,令我们自豪的——我们,是哈师大中文系西藏班,我们没有虚度年华! 有人说,西藏是一个做梦都想去,去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天堂。 我觉得,凡是从西藏回来的人,都有难以割舍的西藏情结,因为那里是美丽而又神圣的地方,是一个用诚心去体验过、永远铭刻在心灵深处无法释怀的地方! 离开西藏有几年了,我的心却总是忘不了西藏。怀念西藏的蓝天白云,怀念西藏的神山圣水,更怀念那些曾经同甘共苦的同事、藏汉族朋友,多少次梦中醒来泪湿枕畔。欣慰的是,西藏的朋友尼玛次仁、刘立强、拉巴次仁、米玛、央金、杨红、多吉仁青、顿珠、王积瑞、张红伟、金梅青、向海英……每一次相聚、每一个电话、每一条 年10月,德央老阿妈带着孙女和曾孙来北京了,刚到北京,老阿妈就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已经到北京,非常想念我!听到德央阿妈熟悉的声音,别提我有多高兴,忙不迭的跑去看望她,邀请她们来到家里。老阿妈特别开心,用一口流利的标准普通话给我讲拉萨的许多新鲜事儿、西藏藏医药大学发生的新变化,还告诉我她家院子里的葡萄树又结满了葡萄,吃不完,很想给我带些来。德央阿妈穿着典雅的藏装,身体还是那么健朗,面色还是那么红润,笑声中永远是那样充满幸福感。送别时,我们恋恋不舍地相拥约定:明年再来! 年10月,西藏民族大学迎来建校60周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亲致贺信。我和朱凤相应邀前往参加庆典活动。回到曾经工作二十多年的民大校园,老校区焕然一新,新校区初见规模,综合办学水平大幅提高。老朋友们相见分外亲,手拉着手说也说不完的知心话。 年9月,大次仁教授来京参加中央党校西藏民族干部第69期培训班,利用周末时间来家里看望我们,还送来一幅寓意健康长寿的白度母唐卡,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深情。 年11月,西藏藏医药大学迎来建校30周年校庆,学校邀请我前往拉萨参加庆典活动。西藏藏医药大学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多么想回去看看啊!但由于身体原因而未能如愿成行,万分遗憾。 年12月,白玛贡桑陪夫人卓玛来京开会。老朋友相见,一起回忆那些曾经的往事,一起去游览五台山,还相约明年两家结伴游三峡。 …… 西藏岁月让我无法忘怀,往日一幕幕的人生片段时不时涌现眼前挥之不去。 终于有一天,我萌发出想写点什么的念头。起初原本只是打算写一篇散文,没想到开了头就一下子收不住了。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激情的催动下写成了一部小书《格桑花开》,仅以本人大学毕业赴藏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成长足迹为主线,以日记、笔记、信件、回忆为基础,以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为素材,从一个哈师大中文系西藏班侧面记录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大学毕业生投身新西藏建设、在艰苦条件下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过程。从西藏教育和新闻出版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西藏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视角,赞颂民族团结,讴歌“老西藏”精神,赞美西藏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幸福生活。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在雪域高原呈现出无限光明的发展前景。 写作过程中,我一次次被感动,经历着心灵的洗礼,写着写着难抑感慨激动,几度哽咽。四十多年来,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以及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大学毕业生和援藏干部,不辱使命,艰苦奋斗,为建设新西藏无私奉献,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只因个人水平有限难以企及,只能取其一隅,以花喻人。 在母校七十华诞之际,我们中文系西藏班全体同学,捧起洁白的哈达,撷取吉祥的格桑花,献给我们的母校,献给我们的老师,感谢母校和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昨天,母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今天母校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我们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我们向母校报告:我们永远是哈师大中文系西藏班! 感恩母校!感恩老师! 敬礼! 作者:哈师大中文系西藏班学生李雅君 执行编辑:李佳香 责任编辑:张微微 图片来源:网 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